随着生成式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渗透进越来越多人的工作、生活之中,为人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其引发的著作权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多,“奥特曼案”等AI生成内容侵权案件也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讨论,至今未有定论。由于AI生成内容的方式与传统情形下纯人工创作作品的方式存在本质的区别,以至于在传统情形下天经地义的、无需明文表达的隐含前提与基础都已经被颠覆,因此用传统评判标准与路径对生成式AI背景下的著作权问题进行评判及规制存在显著障碍。笔者将从这些颠覆性的差别切入,对生成式AI情形下的著作权相关问题进行剖析,以期为化解相关困境提供一些路径启发。
一、AI生成的内容是否属于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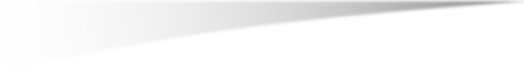
《著作权法》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将上述规定中相关定义的要素提取出来便可看出,“作品”是一种“智力成果”,而“创作”是一种“智力活动”,创作是直接产生作品的过程。
在传统情形下,创作人头脑中有独创性的构思,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将想法表现为文字、音乐、美术等一定的形式,便形成了作品。作品最终呈现的样貌完完全全取决于创作者的思维与行动。以文字为例,文章完全体现作者的脑中所想与笔下所写,不存在提笔写下短诗,纸上却自行出现长篇小说的可能。
在生成式AI的情形下,创作作品的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AI使用者不再需要构思作品的整体样貌,而是仅提供一些想要创作的作品所具备的特征线索,以一定格式的指令提供给AI,由AI根据这些指令生成作品。AI使用者无法完全预料人工智能最终输出作品的精准样貌,最终作品仅是使用者意图的延伸。
有部分观点(例如上海金山区法院“《斗破苍穹》美杜莎形象侵权案”)认为,由于上述差异的存在,AI使用者对于AI的生成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智力投入,故AI的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此类观点目前并不占主流,即大部分学术及司法观点仍然认可AI生成内容可以落入《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范畴。笔者认为,此类观点犯了颠倒因果的谬误。在《著作权法》范畴下评价“作品”与“创作”两个法律概念时,“作品”为因,“创作”为果,不能倒置。
换言之,在法律范畴内,因为一件事物可以被评价为“作品”,所以其产生的过程可以被评价为“创作”,而绝不是因为一个过程可以被评价为“创作”,所以其产物可以被评价为“作品”。笔者持此观点的原因在于,《著作权法》中详细列明了作品的各种类别,而未规定创作过程的类别,因此只能根据作品的形式纳入《著作权法》来评价。并且,作品的形式是相对稳定的,而创作的过程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飞速变化的。以作品为依据评价行为,则法律依据稳定,法律效果统一,在公众心中也是可预期的。
假如根据是否构成“创作”而评价是否构成“作品”,将导致超脱传统认知的新形式创作过程变为无法可依的“法外之地”。在生成式AI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若不纠正此类观点,毫无疑问将极大地助长利用生成式AI进行侵权行为的风气,极大损害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与创作热情。法律解释不应当与公序良俗背道而驰,无视现实地一味将传统评价标准套用到生成式AI的情形下的智力成果认定将产生极为荒谬的示范效应。本文后续部分将基于满足相关条件的AI生成内容可以构成作品的前提进行展开。
二、生成式AI情形下著作权侵权的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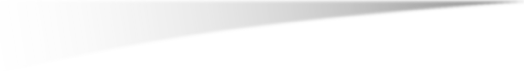
要评价AI生成内容的侵权问题,首先需要从与创作相关的全过程说起。人并非生而具有创作能力,而是先从外界获取信息(既包括前人创作的作品,也包括眼前所见、耳中所听等非作品信息),并从中吸取、分析、归纳特征要素,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与能力。此过程为从具体到抽象的学习过程。当创作者创作作品时,则以自己已经形成的内在创作风格与能力为基础,辅以新创作品的特定主题、创意等,将内心的想法呈现为具体的作品。此过程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创作过程。学习过程为“厚积”,创作过程为“薄发”。作品从无到有的过程仅体现在“薄发”中,但是对于创作而言,仅形成作者的风格与能力而不产生任何作品的“厚积”过程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生成式AI的情形下,虽然部分工作不再需要人完成,但并不代表前述过程中的要素实质性缺位。探究AI生成作品的全过程,会发现除了AI使用者之外,还有AI研发者(包括大模型研发团队、数据采集与加工团队等人员)。AI研发者采集并加工相关数据,并利用其训练出具有创作能力的AI的过程,便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学习过程。AI使用者将指令输给AI并生成作品的过程,便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创作过程。由于AI这颗“外置大脑”已经根据大数据抽象出相关特征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能力,AI使用者无需再额外进行学习过程。在生成作品的过程中,AI使用者仅需提供关键指令,AI承担实际操刀的角色。
传统情形下,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基本规则为“接触+实质性相似”。换言之,除了某些特定抗辩理由外,创作者接触过在先作品以后,便承担了保证自己的作品与在先作品不实质性相似的义务。这一规则适用的隐含前提是,创作者必须完全基于自己的风格与能力创作作品。该前提在传统情形下是天经地义、根本无需赘述的公知常识,但生成式AI却将这一隐含的前提进行了根本性颠覆。在生成式AI的情形下,与在先作品接触的并非AI使用者,甚至AI研发者也可能并不详细知晓在先作品的具体内容。AI研发者难以对海量用户利用其AI生成的作品进行一一审核,实际掌控最终作品的AI使用者有可能由于并未接触在先作品,而无法判断是否侵权。因此,“接触”在先作品者与有机会判断作品是否“实质性相似”者并不相同。
当AI产生过程与在先作品接触且AI生成作品与在先作品实质性相似时,若一味要求AI研发者承担侵权责任,则因AI研发者对最终作品难以知晓而有失公允,同时也将严重阻碍AI产业的发展;若一味要求AI使用者承担责任,则与“接触”规则相抵触;若一味认定其不构成侵权,则对创作者的权益保护极为不利。可见,若将“接触+实质性相似”的传统规则当作金科玉律,在生成式AI的情形下仍不加任何变化地原样照搬,则会陷入各方合法权益无法兼顾的窘境。若要破除窘境,则应当基于行为主体的差异性,将“接触”与“实质性相似”分开来讨论,将原本作为整体的责任进行细化,依据各主体的行为特征进行责任的分摊。
1.AI使用者责任
在著作权侵权的领域,“实质性相似”是侵权判定的起点,无“实质性相似”则无任何讨论其他侵权要素的必要。AI使用者是AI生成作品这一行为的发起者,也是特征指令的输入者,更是最终作品的发布者,理应对侵权行为承担直接责任。但是对比于传统情形下的著作权侵权责任,AI使用者的责任范畴更小,其中不应包括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责任,原因在于AI使用者对于AI学习过程中接触过的在先作品的具体内容既无从知晓也无义务知晓。
根据AI使用者的行为,其应当承担的是输入指令及发布作品两个环节的相关责任。输入的指令虽然不能完全决定最终产品的精确样貌,但是仍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默认AI使用者知晓此事,并且由此确定AI使用者在这一环节中的审慎义务,即应当确保指令中不存在引导AI生成内容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既包括著作权,也包括肖像权、名誉权等其他权利)的部分。关于发布环节,虽然AI使用者可能并未接触在先作品,但是对于AI训练环节可能使用了大量作品训练模型,因此其生成内容可能存在侵犯在先作品著作权风险这一事实,笔者认为AI使用者应当具有知悉义务,因而也具有对发布内容的合理审查义务。该义务可以通过用户协议重点提示,或者法律法规以明文规定等方式加以明确。
对发布环节的评价,可分为发布前和发布后。发布前,AI使用者应当对AI生成内容进行合理审查,若其中有明显侵权的内容则不应当发布。此环节应当依据“接触”规则(此处指AI使用者是否接触过在先作品)进行审查,不应扩大AI使用者的责任范围。发布后,AI使用者对于可能存在的侵权反馈(包括作品评论、侵权告知函等)应当进行及时响应,若有显著证据证明存在侵权,则应当及时删除作品,否则应当对后续侵权损害结果承担侵权责任。
2.AI研发者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传统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并无完全对应AI研发者的法律主体,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对AI研发者的责任规定较为笼统。有部分观点分析AI研发者责任时,直接套用《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传统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定。笔者认为,此类观点并不准确,需要区分AI研发者是否提供了作品发布、传播的服务。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概念规制的是平台存储、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行为,并非所有生成式AI都具有此种信息平台性质的服务;其次,无论生成式AI是否提供了上述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定都无法评价生成式AI研发者在作品全生命周期中承担的更主要的角色应当承担的责任。
笔者认为,AI研发者最需要被评价的,便是其在AI学习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对此可以借鉴和参考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中的有关规定。AI学习时,需要采集并加工海量数据,用于训练大模型。对于此过程的合法性,首先,应当保证数据的采集过程合法,防止使用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的作品;其次,应当确保数据不具有侵权倾向性,防止过度采集并使用某类被侵权作品进行训练,导致使用者的非侵权指令生成的作品倾向于侵犯该类被侵权作品。
仅为了训练AI而对现有作品进行复制、存储、使用的行为是否侵犯著作权这一问题,是目前争议最大、讨论最激烈的点。例如,同样是由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关于奥特曼形象被侵权的案件,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被告存储奥特曼作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依据在于《著作权法》中关于复制权的规定;杭州互联网法院则认为该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原因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设与发展,需要在输入端引入巨量的训练数据,其中不可避免会使用他人作品”。笔者认为,该过程不应被评价为侵犯著作权,原因在于不应当无视合理使用的可能性而机械理解法律条款,仅凭行为符合《著作权法》中关于复制权的行为特征就认定侵权。如前所述,该学习过程与人类的学习过程本质上相同,都是从中提取相关特征以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与能力,而非将作品本身内容所蕴含思想与情感展现给他人的使用,即该过程属于“非表达性使用”。学习过程本身的产物是AI大模型,而非AI生成内容。因此,该过程中对在先作品的使用应当与个人出于学习目的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相同,都应当被认定为“合理使用”,不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也不需向其支付报酬。
若AI研发者采集数据后,除了训练大模型外另作他用,导致侵权,则应当另行评价,与学习过程无关。例如(2024)湘0105民初3790号案件中,被告将原告的作品存储于被告服务器中,并且提供针对这些素材的加工服务,使公众能够获得相关内容,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转播权。如前所述,若生成式AI同时提供了作品发布、传播的服务,则应当同时遵守关于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当AI生成作品侵权时,不应一刀切地将责任全部归结于某一方,而应该结合与AI生成作品相关的全过程,在个案中深究出现侵权的真正原因,在对各方行为进行拆解后,厘清各方应当承担的合理责任,同时避免因角色定位混乱导致的权利义务失衡。
三、AI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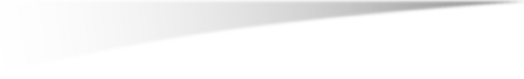
基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前文对各方义务的分析,便不难看出各方应当享有的权利。由于AI使用者对AI生成内容承担直接责任,因此若AI生成内容构成作品,则其著作权应当归属于AI使用者。传统创作过程中,作品完成时便完整体现了创作者意志,著作权随之产生,不以发布为前提(本文不讨论外国人、无国籍人作品的情况)。与传统创作过程不同,在生成式AI的情形下,AI生成的内容可能并不符合使用者预期,因此可能存在使用者重复生成内容或对不同内容进行筛选、后期加工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若AI使用者对AI生成内容的呈现样貌进行过后期加工,则使用者在加工过程中进行了实质性的智力投入,加工完成时著作权便产生,该著作权的客体为加工后的作品;若AI使用者并未对AI生成内容进行实质性加工,则AI生成内容无法被认定为体现了使用者的创作意志,仅当使用者将其发布后才可证明该作品被认可,故应当以实际发布作为使用者享有著作权的时点,著作权的客体为实际被发布后的作品。
从AI研发者享有的权利而言,AI本身仅具有创作的能力与风格,而不具有创作意图,因此AI本质上还是提供创作服务的工具。因此,无论从公平合理的商业模式与商业利益的角度,还是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角度,AI研发者应当仅有权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相应收益,而非享有与AI生成作品的著作权相关的权利。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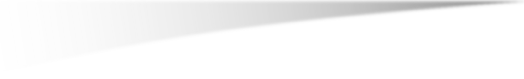
由于生成式AI为新兴技术,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尚未完善,所涉观点的混乱状态仍不合理地扩大或限缩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只有准确分析各方角色与行为,才能确立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对侵权责任合理划分,从而在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文 章 作 者

邱东黎
上海中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
清华大学 本科
总参谋部第五十六研究所 硕士
工作微信:13771098481
qiudongli@ilandlaw.com
专业领域:知识产权;证券与资本市场;公司综合;民商事争议解决

电话:(021)80379999
邮箱:liubin@ilandlaw.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27层
加入我们:liubin@ilandlaw.com
 中岛微信公众号
中岛微信公众号